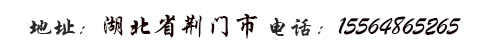飞魔幻middot宫女试嫁
|
楔子 八年元宵,和硕公主府花灯走水。 全城禁灯十六年,直至固伦公主出嫁,慈宁宫大宴,点灯。 一 宫灯十里,星火攒动,遍地红花。 慈宁宫中,固伦公主正在太后和驸马族中女眷的注视下缓缓走向宫门,拖地的大红喜袍上绣的是红鸾鸣动、合欢花开,两路红灯依次高高扬起,宛如羞涩的嫁娘掀开的盖头。 “哇,好大的排场。” 在这灯光璀璨的深谙角落里,慈宁宫身后废弃的小花园一棵歪脖子大槐树的树丫上,跨坐着小宫女红鸾。听说固伦公主的喜袍上绣着传说中的“红鸾鸟”,红鸾瞪大了眼儿想要一窥究竟,入眼的只是满目的红。 与这火红的阵仗相对的是挡不住的寒风,今年的冬天来得似乎特别早,让红鸾不自觉就想起了八年前她第一次遇见他的那个冬夜。那晚也是这样冷,她爬到树丫上坐着,腿冻麻了动弹不得,正急得快要哭出来,突然就撞到“他”。 只记得他梳着特别漂亮的发髻,露出一口大白牙,优哉游哉地看着抱住树丫的她,漫不经心地问:“你怎么上去的?” “……不关你的事。” “你怎么上去的是不关我的事,可你怎么下来就关我的事了。”他翻着白眼,有些坏笑。在她诧异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他已经高高举起了双臂:“信我你就跳下来。” 他乌黑的眸子就和那发髻一样流光熠熠。“我会接住你的。” “啊?”红鸾大眼瞪着这素未谋面的男孩,努力掐了一把自己已经不能动弹的腿,一闭眼,一咬牙,索性就放开了手。 风好凉,夜好深,耳边飞逝而过的仿佛是生命的声音。 一瞬间她觉着自己那只叫做红鸾的大鸟,那是一种她从没见过却特别熟悉的大鸟,特别轻盈,特别艳丽,特别美好。 仿佛属于它的,都应该是极美好的。 于是,她投入了一个美好的怀抱,陌生却温暖的气息。她的双手不自觉地就绕上了他的脖子,心怦怦怦怦跳个不停,好久才睁开了眼,满眼只是他比黑夜还深的头发。 他笑着放开她。谁知道她的脚一落地,突然就眉头一拧。 “……腿、腿麻。”她羞得脸红红的。他转了过去,低下了身子:“来,我背你。” “不要。嬷嬷说,女孩子只能让新郎背,否则会败了名声的。” 他突然转过脸来:“无妨,我是太监。” 红鸾一愣,再一回过神的工夫,他已经不容分说地把她背了起来。红鸾小手绞着握紧在他胸前,小声说:“我叫红鸾。红鸾是一种鸟,仙鸟,特别好的兆头。你呢?” “嗯?”他想了半天,说,“我叫小喜子,因为我长得喜庆。” 那一晚上,路仿佛很漫长,她趴在他的背上,看着他的发髻,听着自己的心跳。 月光一直很好,夜风也不那样冷得难以忍受了。在这不准上灯的深宫中,黑暗的小径上,他背着一只叫做红鸾的大鸟,招摇而过,宛如这世上最自由的人。 “小喜子怎么还不来,再晚就看不到这好戏了。”红鸾趴在树上摆着两条腿百无聊赖地等着。远远的保和殿那边咿咿呀呀地唱开了大戏,圣上正宴请着驸马爷,而眼前慈宁宫也噼里啪啦地耍起来,太后也正宴请驸马族中的女眷。 本是最招摇的红灯一时成了配角,风一起,灯火仿佛稍不留神就会灭了,那样脆弱。 “喂,什么好戏等我来看呢?” 红鸾猛地往下看,看到了他。 “今天固伦公主穿得可真漂亮,听说喜袍上还绣着红鸾鸟,你的眼力比我好,快来帮我看看长成什么模样?” 小喜子杵在那里不动,没好气地说着:“原来就是这出戏啊,没什么意思。那鸟画得丑极了,比不上你的千分之一。” 红鸾羞红了脸,轻声说:“讨打呢,小心公主听到了砍了你的脑袋。” 她看着树下的人:“小喜子,我的腿又麻了。” 他高高地扬起手臂,依旧那样说着:“跳吧,我会接住你。” 二 固伦公主的出嫁宴办得有声有色,各种流言充斥着这百无聊赖的深宫,为这渐冷的天增了一丝人气。 “小驸马爷是和硕公主府唯一的香火,太后对他也是极看重的,总宣他进宫来,时不时还住一段日子呢。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和咱们固伦公主就好上了呢。” “小驸马爷福大,他额娘福更大。当年和硕公主和驸马双双葬身火海,唯独她活下来,不仅如此,还怀上了驸马的骨肉,更绝的是,还是个男孩。” “若是女孩又如何?”红鸾在一旁扫地,多嘴问了一句,却惹得那八卦的人一脸小心,低声说:“当年太后有话,若是不能为和硕公主府留后,大的小的,一起咔嚓——” 红鸾看着那在脖子前明晃晃闪过的犀利姿势,差点一个趔趄。 “所以说啊,这伺候主子的都是在老虎嘴里拔牙的生计。就拿固伦公主宫中那些个丫头来说吧,这些天都小心翼翼生怕踩了母老虎的尾巴。” “怎么,难道她们又惹公主生气了?” “咦,你们没听说吗?固伦公主出嫁循礼是要挑个身边的宫人做试婚格格的呀!这试婚格格要随着礼提前嫁到驸马府去和驸马圆房,来日秉了驸马能否人事,性子是否和顺,这公主才能出嫁。” “那个被选为试婚格格的宫人,岂不成了公主的眼中钉肉中刺?” 红鸾心思很乱地扫着已经扫过的地,又扬起旧的尘土,混混沌沌看不清轨迹。 她寻思着,还是和小喜子做个对食好啊,至少脑袋保住了。再一想,不对啊,小喜子从没说过喜欢她啊? 更一想,她什么时候说过喜欢小喜子了! 红鸾羞着脸拼命挥舞着扫帚,心乱得像一团麻,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心尖儿上突然就开花了。 一定是被固伦公主的喜事给冲昏了头。 正想着,扫帚扫到一双靴,抬眼一看,是从不曾来过的慈宁宫的掌事太监。 “谁是红鸾啊——” 红鸾手中的扫帚突然落了地,有些呆滞地看着他,躲无可躲,逃无可逃。 “你的好日子到了!” 红鸾想起方才那些话,止不住地打了个激灵,听成了“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慈宁宫中,红鸾颤抖着不敢抬头去看太后老祖宗。 “你就是红鸾吗?抬起脸来。” “放肆,太后问话,还不赶紧应着?!”被太监一呵斥,红鸾浑身一抖,慌忙抬起脸,上面端坐着太后,周遭立着五颜六色的娘娘主子们,还有一位和她年纪相仿的美丽女子,清冷的神色不曾有一丝半点暖意,淡扫了她一眼,是说不出的冰寒。 那摇曳的身姿看着却有些眼熟。突然灵光一闪,红鸾一个激灵,这莫不就是那天看到的那个大红喜袍的背影? 眼前的竟然是……固伦公主?! 红鸾正走神,突然太后就开了口,声音极轻,分量却重,最关键的是,红鸾一个字都没听懂。 “嗯,是个福相,名字也好,正合驸马府求的好兆头,怪不得向公主要你。” 红鸾云里雾里的,木然地看着那高高在上的太后老祖宗,看着她嘴皮子一张一合说:“带她去沐浴更衣,保和殿谢了恩,随着礼一起去了吧。” 懵懂之中,她就这样被塞进红彤彤的轿子里,就像是一块要上桌的年糕,浑然不知自己是朝着出宫的路去了。撩开小小的一块布,只看见巴掌大的天,那曾经是她熟悉的一切,渐渐地远去了,那些她跑过的路,转过的弯,那些她见过的没见过的人,那些在风中飘浮的没有着落的红灯笼,明明是喜庆的颜色,却那样脆弱。 “我们这是去哪儿?” 跟在轿子边的小太监有些谄媚地说:“恭喜主子,您被选为试婚格格,一会儿到了驸马府,再和驸马一道领旨谢恩吧——” 红鸾的脑子轰地炸开了。 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出宫。小喜子见多识广,告诉过她那宫外面好大好热闹,有很多女人,也有很多男人。可她此刻却没心思去看。满目摇晃的无尽深红之中,闪过的是方才那女子眼中的寒光。 那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固伦公主,而自己就是那根钉子那根刺。 一路被迎到驸马府,红鸾记得嬷嬷说过新郎会背着新娘入洞房,可是她的“新郎”可是小驸马爷,怎么可能见得到?便只是隔着盖头昏天暗地地谢了恩后,被喜婆接进屋子连带着叮嘱:“格格是替公主来的。今夜和驸马圆房,明早我来探消息,有什么该说的,定要本本分分地说。” “……该说什么?”红鸾掀开盖头的一角,喜婆笑得贼眉鼠眼的,凑在她耳边嘀咕几句,红鸾听得半懂不懂的,只是不知为何脸一下就红了。 “可我——” “恭喜格格,老身先退下了。”喜婆也不再纠缠,扔下羞赧的红鸾到了新房门口,就跑个没影了。 红鸾自己撩着裙角迈进了屋子,屋子简简单单布置了一下,星星点点的红色,算是应景。算起来,还是窗外的一盏红灯笼,红得最是夺目。 小心翼翼放下盖头来,一时间满世界都只是红色。盖头上蹩脚的彩凤,让她想起那天看不真切的红鸾鸟的绣图。她也要像公主一样出嫁了吗?可那个男人究竟是啥样子的?像小喜子一样吗?一样温暖的怀抱吗?一样痒痒的鼻息吗?一样跳得不行的心跳吗? 可惜那终究不是小喜子啊! 宫墙隔了两重天,此生怕都见不到了吧。 不知为何,从未尝过难过滋味的红鸾,心里像是被什么给抽了似的,突然就绷紧了,说不出的疼。 这疼痛,随着“嘎吱”一声门的开启,更加惨淡。 进门的男子步子很轻,动作也很温柔,他不着急掀开盖头,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她身边。榻子凹了进去,红鸾心头一个激灵,下意识地朝旁边窜了去,可是手却被他紧紧地攥住了。 “你!你干什么?!”脱口而出后,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个人,就是她的夫君了。 不知名的恐惧袭上心头,她的手微微颤抖着,扣住了他手背上的肉,他似乎低声沉吟了一下,然后隔了老远,“呼”的一下,吹了蜡烛。 黑夜让一切沉寂,也让红鸾彻底沸腾了。 抱着一死百了的心,她自己猛地掀开了盖头,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盯着那张脸的轮廓打量,看不清鼻子眉眼,只是看见高高的官帽,黑黢黢的,甚是吓人。 他的手还是不放开,温度越来越炽热。 “放开我。”她试图挣脱,他却先松了手,谁知道还没松一口气,已经感觉脸上多了一丝被抚摸的触感,她一个激灵,毫不犹豫地就是一口狠狠咬了上去。 “你什么你!大不了就赐死吧,本姑娘才不怕。” “想不到红鸾主子出了宫脾气又见长啊!”男人低声笑了,红鸾像被雷劈一样愣住了,他的脸慢慢地探进照着榻上的月色里,那鼻眼那轮廓,竟是—— “怎么?认不出了吗?那这样呢?”他露出那熟悉的发髻,狡黠地眨眨眼,就像八年前初见的那个少年。 “可怎么会……你不是太监吗?”红鸾还懵懂着,就看见他一阵坏笑,突然意识到自己八年来都被骗了,一个劲儿地捶打着他,“还敢说叫人家信你!信你!信你个大头鬼!” “快来看看我这个鬼头大不大?” 红鸾的手指在他的牵引下深入他的头发,柔软的密发,如初见时的模样。她突然扑腾一下站到了床上去,他一扭头,她直接扑到了他的背上,小手紧紧地扭在他的胸前。 “背我。” “什么?” “你已经坏了我的名声了。”她小声在他耳边说着,然后浅浅地亲了一下他的耳垂,他一个激灵,她再一回神的时候,已经伏在了他宽厚的背上。 “哈哈——”她大笑着,“红鸾飞起来了——” 他背着她在这狭小的屋子里旋转,仿佛天地都是他们的,一直都是,永远都是。那红灯一直都在角落,闪着不起眼的红光,却能照满全部的世界。 灯灭,红衣落地,屋里屋外同样炽热地烧过,然后是入夜的凄寒无声。 三 大婚如期而至,红鸾的出现连个插曲都算不上。和硕公主府门前挂了高高的大红灯笼,它们随风而起,似火的仪仗。 公主她还是来了,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女人,就这样生生地要在同一屋檐下,叫着同一个男人夫君。 不知为何,红鸾却不记得那日殿上满眼寒光的公主。她记得的是她穿着大红喜袍走在慈宁宫中的背影,风姿绰约,风华万千,红鸾鸣,合欢开,多盛大的光景。 可原来那却是别人的好光景。 失落地退一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一回身却是一身素色的妇人远远地站在那里,盯着她,很有些面善。 “大喜的日子,您不穿红吗?”红鸾怯怯地问了一句,在府中多日,她仍是个外人。 “我是未亡人,这样的日子不适合我。” “您是——”红鸾猜着,又不敢说出口,那妇人淡淡地应着,“你该叫我一声额娘。” 不知怎的,这句一出口,红鸾和那妇人都静默了,仿佛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层层蚕丝密密地织着,将本不相识的两个女人,如此牵连在一起。 “额娘。”红鸾没有多想地叫出了口,那妇人突然一个恍惚,红鸾上前扶住了她,她却反身钳住她的手腕,然后眸子一点一点地细细地打量着红鸾的脸。 年轻的标致的一张脸,那么有朝气,还有些小女子的脾气。 “你该梳妇人的头了。”侧福晋突然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已经是个女人了啊,都没人为你多想,也是,今天迎娶公主,试婚格格又算什么。” 这话听起来,没有半分嘲讽,说起来,倒满是悲愤。 红鸾就在这样一个喧闹的时刻,被这个静静的妇人拉进屋子对镜梳妆。她有一双巧手,梳子在她手里仿佛是活的一样,她为她梳头,就像额娘送女儿出嫁一般。 “其实我也一直想有个女儿的。”她自言自语着。 红鸾心想,多亏不是女儿,否则您早就被“咔嚓”了。转念一想,这样大不敬的话,还是烂在肚子里的好。 “那我做您的女儿吧。”红鸾无奈地说着,“反正我也不能名正言顺地做您的儿媳。” 侧福晋手一抖,然后灵巧地绾了个妇人寻常的发髻,似是无心地说:“我没有女儿。” 红鸾看着镜中如常的她和惨白的自己,一前一后,两个妇人,仿佛二重影,叠在了一起。 入了夜,府上挂起了大红灯笼,就像宫中喜宴一样。红鸾被安排在偏房,抱臂站在门口形单影只,回忆着前夜做梦般的温暖。 恍惚中,看见一个黑影提着一盏灯来了,刚想叫出口,才发现来的只是丫鬟。 “喂,公主恩赏的年糕,下人们都领了,独你这份要亲自送来,真是架子不小。” 红鸾听了眉梢动了动,微微一欠身,那丫鬟鄙夷又忌妒的神情一览无余。“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试婚格格吗,说破天就是陪床的奴才。” 正说到这句,两人身上那点红光突然被窜出的黑影给笼了,凭空炸出一句话:“给我滚蛋!” 下人惊了,红鸾也惊了,在这大喜之夜,他居然来了,披星戴月地来了,义无反顾地来了。 “驸马爷——”下人委屈地应着,高高端起年糕盘子,“我只是奉命来送恩赏的。” 他皱着眉头看着被红衣包裹着的年糕,又看了看红鸾惨白的脸色,低声说道:“小小贱命,何须恩赏。” 红鸾倒吸一口凉气。这话明里说的是她,可实则指的是他自己吧? 抢在前面拦住下人,红鸾稳稳接过了盘子:“恩赏我收了,谢谢。”转而她绽放给他一个最艳丽的笑容,“我最喜年糕了。” 他终于笑了,仿佛再自然不过地牵起她的手,当着那下人炯然的目光,旁若无人地说:“那我陪你吃。” 红鸾瞪大眼睛,努力撇着嘴,男人只是宠溺地抚摸上她的脸:“看你这模样,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屋内,红鸾故意背着他坐着,噎着年糕,口中的话模糊不清。“你若是被赐死了,请不要拉我垫背。” “是谁说过我若去了,要吹吹打打送我上路,喜喜庆庆的?” 红鸾没想到当年的话他竟然字字句句都记得,心中一股暖意,脸却还板着:“你走。” “那我可真走了。” 随后,一声不小的关门声,红鸾惊得转身,夜风随窗入了,入了冬吹不尽的寒意,嘴里是温热的年糕,脸上冲刷出更热的水痕。 仿佛在追着一个影子,她站起来伸出手去,阴影中,慢慢伸过去,他的鼻息拂过手指,然后是浅浅地啄吻。 “没有红鸾主子的恩赏,我怎么舍得走啊!” 他将她撞入了满屋的月色中,一片银白无影,唯有彼此。他狠狠地吻着她,只是那吻好冰冷,冷得让她不禁颤抖。 “等元宵节的时候,我会带你去看京城的灯,比宫中的还漂亮。” 红鸾看着他眼中的闪烁,无可奈何地笑了,突然说:“你能不能现在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不会是让我给你做个花灯吧?我可做不来。” “我不要花灯,我想要些能长久的。我想你给我写几个字,就挂在我床前,我天天一睁眼就看得见。” “哪几个字?” “一首诗。” “你还会念诗?” “我自然不会,只是听养大我的嬷嬷说过,我的名字是一句诗。她觉得意头好,就向宫里有学问的人问全了,念给我背着,以后嫁人了可以讨婆家欢喜。” “你来说,我来写。”他展开笔墨,墨点在白绢上慢慢晕染开。红鸾浅浅吐气—— 红鸾多情无悲鸣,犹得天喜嫣然姿。 不向瑶池凤阁居,偏向世间一良人。 四 驸马大婚之夜住在试婚格格那里,这事连太后都惊动了。不日驸马就被宣入了宫,劈头盖脸被骂了一顿,临了,太后竟放话出来:“什么人生什么种!” 他猛地抬头,却不敢顶嘴,胸中憋了一口恶气。回到府中远远就看见红鸾跪在园中,高高举着一整盘年糕,露出的手臂全是伤痕。 他上前去直奔了那个端坐在堂上冷冷的女子,翻起的衣襟从红鸾耳边滑过,这才让她从半昏之中惊醒。 “这是做什么?”他厉声。 “恩赏。”公主缓缓地说着,仿佛这本是一件极微不足道的事,那端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听说你挑了她是为了‘红鸾’二字,要讨个好兆头。可我觉得年糕才是更好的兆头,从今往后,就叫她年糕了吧。” 仿佛是商量好了一样,下人们迎合地笑了起来,在这嘲笑声中,红鸾高举年糕托盘的手臂忍不住地颤抖,想起出宫时就觉着自己像是人家桌板上的年糕,没想到,这戏言却成真了。 “够了。”他拧紧了眉,“不要再胡闹了。” “我胡闹了吗?”公主微微抬眼,歪着头,打量着他身后那不住颤抖的女孩。她本该独有他的,为何会冒出一个什么试婚格格来?天大的笑话。 “是我胡闹了。”他读懂了她的字里行间,猛地抬脸。是他胡闹了,他不该由着自己的性子,把红鸾带入这是非中来。 他从来都不是个自由的人。 从小就懂得察言观色,谁是圣上,谁是太后,谁是公主,谁是能让他们母子活下去的人。 每次进宫奉命陪着公主玩,哪一次不是违心地笑,哪一次不是受辱地让,哪一次不是偷偷地哭?他曾无数次发誓再也不要进宫,可回到那座大火烧尽的鬼宅,看着额娘那无助的孤影,听她说,你知道吗?我们要活着,要活得很好,这才对得起你的爹和这府中所有的冤魂。 于是他还是会进宫,仿佛脸上长了面具,直到那一天他走过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那个爬树的少女,一切才终于不同了。 她成了他每次入宫的唯一动力,只是他不能告诉她自己究竟是谁,也不敢给她任何承诺。直到太后说要选试婚格格,他才想当然地以为终于等到了一个转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我想要那个叫红鸾的女人。” 在公主怀疑的目光中,他多余地添了一句:“府中多冤魂,算了一算,她可以来冲喜。” 其实这一切,都和那个名字无关。他只是爱她,八年又四十一天。 他以为他骗得周全,殊不知这世上,最周全的谎话都瞒不过一个时时刻刻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白癜风好呢北京那家医院治疗白癜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angyelv.com/xrzpr/4581.html
- 上一篇文章: 短文宫女试嫁文褪尽铅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