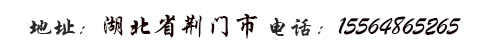在你心上种下仙人掌,想拥抱你却留下一道道
|
文|夏不绿 微博丨 夏不绿Donna 一生所爱 漂泊在白云外 “情不敢至深,恐大梦一场。卦不敢算尽,怕天道无常。” 引 案子开庭那日,吕襄蜓特意选了自己最钟爱的那条红裙,红唇媚眼。她对着镜子用眼线笔细细描绘着,末了从首饰盒里取出那条宝格丽项链戴在自己纤细的脖子上。项链是白普霖在拍卖会为她倾囊拍得的。好多年了,她都快记不清他们相识了多久。他从前总喜欢低声唤她小蜓以示亲密,只是如今要将她送上法庭的也是他。 白普霖,伦敦最好的华籍律师,有小道消息曾猜测他跟伦敦一些不法势力有瓜葛,代理的官司都是非富即贵。但这次,他却接了一个伦敦街头随处可见的设计师侵权案,并把名噪一时的珠宝设计师吕襄蜓告上了法庭。许多记者采访问及此事,对着镜头的白普霖只是一脸淡然的神情,用他一贯不以为意的语调说:“作为一个律师,有义务为更多的大众维权,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所接手的案子都务必经得起良心的拷问。” 吕襄蜓在电视上听到这段话时,不禁哑然失笑。 多少年了,白普霖还是这样一副对得起天地良心的姿态。 01 吕襄蜓,原名林晚晚,三年前因斯嘉丽佩戴她设计的项链走奥斯卡红地毯,而使吕襄蜓的设计名躁一时。她设计的珠宝很多明星都在各大时装秀场上戴过,而告她的人只是她工作室的一个前员工,对方指控吕襄蜓抄袭了她的设计稿。本来这事只要置之不理就好,毕竟没谁真的当回事儿。在这个名利场中,为了搏出位什么手段都能使,何况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的一言之词。可是这案子被白普霖接下后,意义就变得非比寻常了。 吕襄蜓坐在被告席上,见白普霖一身正装,面目坚毅地进行陈述。两三年没见,他变得越发像个沉稳、凡事都会不动声色的大人了。 一审结束后,吕襄蜓没有立刻离开。外面全是记者,她疲于应付他们。工作人员让她从后门坐车离开,白普霖和原告人说完事后,正好从她身边经过。他转头看了她一眼,吕襄蜓也正好看到他,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两人的眸子里都没有任何情感波澜,寂静得就像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很难想象,几年前白普霖还为了她千金散尽只为博美人一笑,如今却成了站在两个对立面的被告与原告律师。 他看到她脖颈上的那条项链,微微一怔,随即明白过来这不过是吕襄蜓的心理战术。他心里冷笑一声,大步走出法庭。 吕襄蜓清楚地记得,她跟白普霖在一起的那几年,她不过是个在珠宝公司做杂事的小职员。白普霖司法考试刚过,因为家里的一些原因,他拒绝接受家里的经济来源。两个人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房间里没有暖气,一到冬天吕襄蜓就会准备两个大的玻璃瓶,灌满热水放在被子里捂暖了才睡觉。 白普霖私下接了一些翻译的活儿,常常忙到深夜。点一盏小灯在桌上。吕襄蜓喜欢把柚子皮扔进火炉里,所以屋子里常常弥漫着果香味。吕襄蜓深夜醒来,见白普霖还开着台灯工作,便悄悄起身去厨房给他煲汤。索性英国人不爱吃猪骨一类的杂碎,吕襄蜓便去市场花极少的价钱买一大包回来,于是每天都可以喝到营养美味的靓汤。 年轻又贫瘠的岁月里,两个年轻人因着爱互相取暖,一碗平凡的汤水也能喝出珍贵的滋味来。白普霖想,此生除了吕襄蜓他谁也不娶,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谁会对他这样好了。 吕襄蜓站在厨房里,面前的砂锅里煲着猪骨和山药,白色烟雾升到眼前,她的眼底也升起一层水汽。窗外大雪铺地,而吕襄蜓心里酝酿着一个秘密。 02 认识白普霖前,吕襄蜓居无定所,在一家酒吧工作。白天不打工就找家小旅馆休息一会儿,或者去咖啡馆坐到晚上上班时间。白普霖当时读大三,虽然常捉襟见肘,但身上纨绔子弟的恶习一直没变,晚上跟一帮朋友混迹各个娱乐场所。 白普霖要了杯伏特加,看了一眼吧台后的吕襄蜓,问:“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吕襄蜓把酒递给他,笑道:“可以换个梗吗?” “你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面前的女孩眉眼深邃,但身上却是典型的中国姑娘的味道。 “从小就在英国,不过我会中文。” “没去过中国?” “没。” 白普霖喝光杯里的酒,又要了一杯。 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吕襄蜓忙碌的身影宛如一只超脱凡尘的精灵。她的眸子很黑,皮肤白皙,总让人想到中国旧时候穿着旗袍的江南水乡的女人。 白普霖喝完酒,走过去,问吕襄蜓:“你几点下班,一起吃个夜宵吧。” 吕襄蜓定定地看向他,像一片沉静的湖投进白普霖心里。本以为她会拒绝,没想到最后猝不及防地给了白普霖一个笑容:“好啊,再过十分钟就能走了。” 两个人走了两条街去中国人开的火锅店吃饭。吕襄蜓很熟练地自己兑好调料,白普霖在一旁看着,不自觉地笑了:“你个英国人居然这么喜欢吃火锅。” “可能骨子里的基因没变吧。”她把端上来的菜放进锅里,开始涮鸭肠。 一顿火锅吃掉吕襄蜓一天的工资,不过钱是白普霖付的。出于礼貌,吕襄蜓觉得自己应该回请点儿什么,于是出门在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了两盒雪糕。一条路通透得只剩他们两人,道旁唯有一家二十四便利店亮着温暖的光。 “你家在哪儿?”白普霖出于绅士习惯,准备送吕襄蜓回家。 吕襄蜓舀了一大勺雪糕喂进嘴里,穷得坦荡甚至带点儿嚣张:“没家,到处借宿。” 白普霖愣了一下,皱了皱眉,尤其是在吕襄蜓说得那么无所谓的时候。 “怎么不找个地方住?你家里人呢?” “都没了。”吕襄蜓吃完冰激凌,把盒子捏扁,扔进路边的垃圾桶,“家里房子也没了,只能每天到处找地方打发时间。” 白普霖突然想到一些事,心被刺了一下,收敛起先前的绅士态度,转而神色凌厉地问她:“你行李呢?” “在酒吧的储物室存着呢。” 白普霖已经大步走到前面去了,吕襄蜓以为他要走掉,没想到他突然回过头来对她说:“去酒吧拿你的行李,暂时住我那里吧。” 白普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两室一厅,自己住一间,另一间拿来堆积杂物,他把杂物全部搬出来堆放在客厅,让吕襄蜓先住进去。 “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可以每个月给我房租。钱呢,等你有的时候再给,没有就欠在那里。”这个提议既免除了吕襄蜓的为难,又让他的收留多了个由头。 吕襄蜓道了谢,把行李搬进去。就这样,她成了白普霖的室友。而这只是一切的开始,朝夕相处的点滴情意,最终汇成河。只是这河水不仅能够载舟,亦能覆舟。 03 吕襄蜓被工作人员簇拥着准备从法院后门离开,结果到了后门才发现,这里照样被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去拦想要窜到吕襄蜓面前的记者们,吕襄蜓见情况不妙,立马转身往回走。她一个人匆匆地在走廊上走着,就在快要迷路的时候,一个身影从转角处走出来。 是白普霖。 吕襄蜓摘下墨镜,望向他,眼里满是警惕和疑惑。 “不是想离开吗?”白普霖冲她挥了挥手,便走在前面带路。 左右也没有别的选择,吕襄蜓便跟在他身后赌一把。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走在前面的白普霖没有回头,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吕小姐言重了,我只是看到你如丧家之犬一样躲避那些记者,有些于心不忍。我想案子是案子,给你私人生活带来影响毕竟非我所愿。” 吕襄蜓冷笑出声:“是吗,那还多谢白律师的体贴了。” 白普霖带她从一条小路离开,他用自己的车载着吕襄蜓出去。汽车从那些记者身边开过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吕设计师居然会坐着状告她的原告律师白普霖的车离开。 见那些记者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吕襄蜓终于松懈下来,倚在窗边原本无懈可击的妆容里显露出疲惫。白普霖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汽车在一家咖啡馆外停下。他下车买了两杯咖啡回来,手里还拿着一盒维生素C片。 吕襄蜓怔了一下,然后接过。 两个人突然陷入尴尬的沉默里。 对她好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吕襄蜓想到从前他们在一起时,白普霖也总是事事照顾自己。刚和他成为室友那阵,白普霖的生活习惯和她几乎是颠倒的,她晚上下班回家,白普霖有时已经睡了。她在厨房煮东西,弄得乒乓作响白普霖听见了也从不生气。他出去和朋友玩,有时会喊上她一起。大家打中国麻将,或者玩扑克,每次回家白普霖都会问吕襄蜓有没有输,输了多少,他会把她输掉的都贴给她。 吕襄蜓总是傲慢地抬起头,不屑地道:“我今天可赢了钱,你怎么好像总是盼着我输似的。” “你连房子都租不起,我怕你输了钱饿死在我家。”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斗来斗去,虽然表面上谁也不退让,但吕襄蜓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好,心里开始动摇。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白普霖指着她大声斥责“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的时候,吕襄蜓只是咬紧牙什么也不说,她知道只要自己一开口就会输。 这并不是什么谁赢了谁的赌局,吕襄蜓从一开始就错了,但她愿意陪他两败俱伤。 白普霖重新启动车子,开出去一会儿后,突然自嘲地笑了,转头看向吕襄蜓:“我都忘记问你家在哪儿了,不知道现在吕小姐住哪里?” 吕襄蜓说了个地方,白普霖依旧笑:“有名的富人区啊。”语气不咸不淡,却像一把锥子直接刺向吕襄蜓。 吕襄蜓没说话,转头看向窗外。汽车飞速地驶过街道,外面的风景像曝光的胶片。她想起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白普霖因为跟家里断了联系,没了经济来源,他们只好搬到更小的房子里去,那里周遭的环境和治安都很差。有一次吕襄蜓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遇到几个混混一直缠着她,当时吓得大脑一片空白。四周没有一个人,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幸好白普霖见她这么晚还没回家出来看情况,及时赶走了那些混混。 吕襄蜓蹲在地上,看得出来吓得不轻。白普霖轻轻抱住她,安慰道:“没事了,没事了,我在这儿……” 那次以后,白普霖就出去找了好几份兼职赚钱,为了攒够钱搬去更好一点的住宅,并且无论多忙都坚持去接吕襄蜓下班。 吕襄蜓想到这些的时候,没意识到车子已经到了自己小区门口。 “吕小姐。”白普霖提醒她,“该下车了。” 吕襄蜓打开车门,临下去前,回头看了他一眼:“我们早就扯平了,如果你这次接手案子是为了看我的笑话,那么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就算你再厉害,白还是白,永远不可能成为黑。”说完这句话,她才下车离开。 白普霖并没有立即把车开走,而是看着她的背影直至消失,最后皱了皱眉,把脸埋进胳膊里,良久缓缓抬起头来,像大梦初醒的模样。 04 第二天,吕襄蜓还没有起床,就接到物业的电话。 “吕小姐吗?”手机那头是物业人员焦虑的声音,“现在记者们都在大门外堵着呢,你待会儿千万别出来……” 吕襄蜓立即起身走到窗台往外看,就看到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她生气地把手机扔到床上,嘴里恨恨地吐出三个字:“白普霖。” 她还是太大意了,下意识地以为白普霖不会绝情到这种地步,黄鼠狼给鸡拜年这样的把戏都没看穿。 床头柜上放着她昨晚睡觉前取下的项链,此时正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吕襄蜓想到白普霖送自己这条项链的几年前,他刚在业界崭露头角。吕襄蜓才开始做设计师,初步接触珠宝设计。为了讨她开心,白普霖带她去参加了一个珠宝慈善活动,吕襄蜓着一身自己设计裁剪的晚礼服,白普霖紧紧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个顽皮的小孩似的,生怕一松手她人就不见了。 宝格丽项链起拍价都不低,来参加活动的大多成双入对,带着女友或夫人。为了博得身边人的欢心,这些男人都不断往上抬价。吕襄蜓见一旁的白普霖每举一次牌子,心就紧张一下,她心里算着这条项链差不多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 白普霖拍得项链后,念了句中国的古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为吕襄蜓戴好项链,告诉她不用担心,花出去的钱自己都可以慢慢赚回来,可项链只此一条,他不想留下遗憾。 吕襄蜓想到这些,不禁心烦意乱,把项链收进抽屉里,打电话给助理,让对方帮自己准备机票和签证,她不能再继续待在伦敦了。这是她来伦敦这么多年,第一次想到要回故乡扬州。 烟花三月下扬州,林家老宅的院子繁花似锦,梨花如雪、桃花拂面、槐树成。春天悄无声息而又隆重。 十几年前,林家老宅古朴的雕花大门被一纸封条封住。还叫着林晚晚的吕襄蜓拉着奶奶的手号啕大哭,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穿着警服的大人们要把自己的父亲抓走,也不明白为何一夜之间她和奶奶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奶奶苍老干枯的手心疼地替吕襄蜓擦着眼泪,安慰她道:“晚晚不哭,还有奶奶呢,我们先去白叔叔家住,以后我们再搬回来啊……” 吕襄蜓父亲经营的公司欠下庞大的债务,其间还涉及一些复杂的民事案件。十岁的吕襄蜓不懂这些,只是害怕,拉着奶奶的手上了一辆汽车。她那时还不明白,她一生的命运将在那一天从此改变。 白叔叔和林家是世交,他唯一的儿子白普霖当时十二岁,个子已经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他和吕襄蜓见过几次,记得有一次她生日的时候去她家玩,很大一栋宅子,据说还被纳为当地保护的历史遗迹。吕襄蜓当时穿着一条白色的纱裙,梳着公主头,头上还戴了一个小小的王冠饰品,被周围的人众星捧月,看上去也跟公主无异。虽然是吕襄蜓的生日宴,但到底还是大人们的应酬。吕襄蜓溜到后院玩,正巧白普霖在那里捉蛐蛐。吕襄蜓没理他,径直走到院子的橘子树下,然后把裙角打了个结,二话不说就往上爬。 白普霖在下面看得张大了嘴,他没见过哪个女孩这么粗鲁的。此时的吕襄蜓已经爬上了树,坐在树干上,摘了个橘子,扒开皮吃起来。她好像这时才意识到白普霖的存在,问他要不要吃,说着就摘了个橘子朝他扔去。 “屋里又不是没有橘子,干嘛跑这里来吃?” “屋里不好玩。”吕襄蜓说,“自己摘的才好吃。” 院子里的桂花树开花了,空气里是浓郁的花香,香得醉人。吕襄蜓吃完橘子,准备从树上下来,结果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超出了自己的预料。她有些茫然地看了看树下的白普霖,犹豫地喊了他一声:“喂,我下不来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白普霖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走过去。幸好他个子够高,他张开双手,很大方地对吕襄蜓说:“你跳下来,我接着你。” 吕襄蜓不信任地看他一眼:“那你站稳了。”说着就往下跳去。 白普霖接住了他,往后退了几步,两个人一起摔在了地上,但有白普霖抱着吕襄蜓,所以她没有受伤。 夜风很凉,吕襄蜓第一次离除了父亲以外的异性这么近,甚至听到了他略跳快的心跳声。 就是那一次,白普霖记住了这个小女孩,不过那时她还叫林晚晚。 吕襄蜓到白家后,白普霖就每天陪着她,可吕襄蜓压根儿不搭理他,或者说除了奶奶以外她不理任何人。 到了晚上,吕襄蜓躺在奶奶身边夜不能眠。她知道奶奶一定也没有睡着,可此时此刻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忍着声音让眼泪往下淌。吕襄蜓翻身慢慢从床上起来,赤着脚走出去,走到玄关的时候再摸黑找到自己的鞋穿上。 出了白家,她一路小跑,她想回老宅把自己和奶奶的东西拿回来。 然而老宅四周都拉了封锁线,幸好她知道后门处有个地方可以翻进去。家里还是原样,她打开卧室的灯,法式吊灯辉煌耀眼,床上和沙发上都蒙着天蓝色的天鹅绒罩面,吕襄蜓拉开罩面,躺在真丝床单上,一瞬间又回到过去,竟不知不觉睡着了。 她不知道这一梦便会与奶奶永别。此后她成为一叶浮萍,漂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来。 她再回到白家,白叔叔非常抱歉地抱住吕襄蜓,告诉她奶奶心脏病发作没有及时抢救过来。吕襄蜓根本不信,踢打着对方说要去见奶奶,哭着让他们把奶奶还给自己。 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心里感到害怕,不相信白叔叔说的一切,也不相信父亲真的会做坏事。过了几日,吕襄蜓父亲过去的一个下属找到吕襄蜓,说带她去见父亲。那是吕襄蜓第一次去监狱,阴森森的,没有一丝温度,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谁会想到这些事全是白普霖父亲从中作梗,父亲让吕襄蜓去自己给的一个地址找到之前存放东西的邮箱,里面有自己为吕襄蜓准备的一笔钱和护照。父亲让吕襄蜓离开国内,只有这样吕襄蜓才能安全。见完父亲后,吕襄蜓不敢再回白家,她哪里也不敢多停留,就立马赶去了机场。从此,她离开了中国,成了一个回不到故乡的异乡人。 为了养活自己,吕襄蜓在伦敦几乎什么都做过。服务生、泊车员、收银员、酒吧服务生……她把赚到的钱存起来,医院做了眼睛和鼻子的手术让自己看起来更加西化。以至于白普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真的相信她是一个从来没去过中国的英国人,而吕襄蜓也终于开始实施她报复的第一步。 05 吕襄蜓常常会想到自己跟白普霖之间的种种,如果他不来伦敦留学,不去酒吧,他们只会是这个世界擦身而过的两个陌生人,再无交集。就像宿命般,注定他们要重逢,然后成为恋人,最后撕破嘴脸,成为仇人。 虽然白普霖跟家里甚少联系,但吕襄蜓还是知道白家跟伦敦的一些势力有关联,所以白父才费尽心力要把白普霖送到伦敦。本来是想让他为家里做事,结果白普霖非但没有接受,还做了律师。两个人吵起来的时候,白普霖总是用法律来回击他:“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犯法的!” “犯法?”白父冷笑道,“你就是靠这些你眼里瞧不上的肮脏的钱长到现在的,你以为你干净正义得很!” 十几年前,白父为了扩大自己的商业范围,不惜栽赃嫁祸给好友林伟,导致其被判无期徒刑。白普霖最无法原谅的是,当时林家的小女孩和奶奶住在他们家,那个老人因为撞破白父的秘密,结果被活生生气得心脏病发作。而之后小女孩下落不明,至今都不知道在何处。所以他第一次见到吕襄蜓,听她一脸不屑地说自己无家可归的时候,他觉得心疼,或许他是下意识地想要为年少时未尽的善意进行弥补。 吕襄蜓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见他工作的书桌上有一只蚊子,便伸手去打,而后语气淡淡地道:“都这么多年了,何必放在心上。”这话与其说是说给白普霖听的,更多的是劝慰自己。 但人心啊,不是那么容易就过去的。吕襄蜓最后利用白普霖抓到了白父的把柄,非常干脆利落地把他送进了监狱。对,就是那个阴森森冷冰冰的地方。吕襄蜓想: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啊,没人能够逃脱的。 而白普霖得知举报人是吕襄蜓的时候,整个人瞬间蒙了,直到再三确认无误后,他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当时在国内处理父亲的事,回伦敦的时候还是吕襄蜓来接的机。一段时间没见,她依然漂亮得如同一个洋娃娃,见到白普霖很自然地便迎上去抱住他。结果收到的只是白普霖冷冷的回应:“林晚晚,你到现在还要继续装下去吗?” 白普霖派人调查了吕襄蜓,知道她就是那个自己心有所欠的小女孩后,久久没说一句话。 吕襄蜓一愣,慢慢收起脸上的笑容,看向白普霖:“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你接近我的目的?”白普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女孩,不敢相信她的步步为营和机关算尽,“你的演技真是太好了,如今你得偿所愿了吧。” 吕襄蜓没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如今说什么看上去都是诡辩。说她是真的爱他?可她一开始确实是心怀其他企图,就算中间有过犹豫,但最后还是毫不留情地毁了白普霖的家。 两人在机场门口分手,彼此都发誓此生不复相见,从此再无联系。后来白普霖因为连赢好几个大案,名噪一时,直至把吕襄蜓告上法庭。 吕襄蜓想到一句话——“情不敢至深,恐大梦一场。卦不敢算尽,怕天道无常。” 无常,说的便是他们。 06 林家的老宅早被改成一个私家园林,二十块钱一张门票。吕襄蜓看到很多人在排队买票,不禁莞尔。她想到一件民间轶事,解放初年,大伙准备把一块写着“大清门”的门牌反过来重新刻上“中华门”,可谁知翻转过来,后面刻着醒目的“大明门”三个字。历史的洪流不仅没放过凡身肉体的人们,也没放过这世间的一草一木,这大概就是它最公平之处了。 吕襄蜓找了一家咖啡馆休息,店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台电视。里面正好在播放一则新闻:“据我台驻伦敦记者报道,位于XX富人区的一所公寓发生爆炸事件,事件原因不明,暂时没发生死伤……” 吕襄蜓手里的咖啡差点洒到身上,她急忙拨通伦敦朋友的电话,询问是怎么一回事。 对方似乎也吓了一大跳,吞吞吐吐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刚知道消息不久。幸好,幸好你不在……” 火灾发生的地点正是吕襄蜓的家,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你什么时候回伦敦?到时我来接你吧,感觉最近发生的事怎么都像是冲着你来的。” 吕襄蜓挂断电话后陷入沉思,脑子飞速运转着。官司、记者、爆炸……这些事在冥冥之中会有联系吗?想到这些问题,她觉得头疼,把桌上的水一口喝完,然后打电话让人帮自己订机票。 一下飞机,媒体记者们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见到吕襄蜓,大家纷纷拥上去。吕襄蜓把帽檐压低,但仍躲不过镜头。 “接下来你住哪里呢?因为前几日你家房子被炸……” “官司还会继续吗?” “对白律师涉嫌参与伦敦黑势力案件的事你有什么看法……” …… “什么?”吕襄蜓抬起一直躲避的脸,看向刚才提问的那个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刚才说什么?” “官司……” “不是这个。”吕襄蜓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你刚才说白律师什么?” “他涉嫌伦敦黑势力……” 对方话还没说完,吕襄蜓便用力将他们推开,几乎是连走带跑地离开机场。 爆炸案已经有了初步结论,涉及伦敦的一些黑势力。至于为何这些黑势力跟吕襄蜓过不去,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警方倒因此寻出一条重要的线索,这些势力曾跟中国籍白姓男子有关系,最后竟然发现这个白普霖竟是其儿子。事情就这样往极其戏剧化的方向展开,在这个新闻出来后,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从抄袭官司转移到了白普霖身上。 吕襄蜓看到这些消息后,心里五味陈杂。她知道白普霖不会参与这些,他向来恨极了自己父亲的做法。可是为什么这么巧,那些黑势力为何想要杀害她呢? 错综复杂的事件走向令她措手不及,而告她抄袭的原告突然就不了了之了。 吕襄蜓找到那个女孩,等在她家楼下拦住她,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方见到吕襄蜓后,像见到讨债的债主似的,有些慌不择路。最后见实在没办法,只好垂下头,一脸歉疚地笑道:“告你这事真跟我没关系,是那个白律师给钱让我告你的,他一下拿出那么多钱,我实在是……” 更多的她也不知道了,吕襄蜓听完她的话后只觉陷入更深的云雾里,寻不到出路。 再见到白普霖是在一个月后的法庭上,他被指控为参与黑帮事务而成为被告。虽然警方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但这件事已经差不多毁掉了白普霖的职业生涯。所有媒体都渲染他是一个伪君子,披着正义的皮囊干尽非法的事。 吕襄蜓坐在下面的席位上看法官宣判白普霖无罪释放。可能全世界只有她相信他是真的无辜。 白普霖也看见了吕襄蜓,两个人四目相对时,白普霖竟对她笑了笑,那笑里多是无奈,像是在说:瞧,我也有今天。 吕襄蜓不会知道的是,白普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护她周全。从找到前员工告她抄袭,到泄露她的家庭住址给记者,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故意的。 几年前她扳倒了他的父亲,导致伦敦这边的生意瘫痪。虽然白普霖费尽心思想要藏住关于吕襄蜓的所有线索,但最后还是被他们找到,并计划实施报复手段。白普霖实在没辙,这才想出用媒体的北京有没有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北京白癜风治疗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nrenzhangaxrz.com/xrzpr/1076.html
- 上一篇文章: 拥有高颜值有创意的杯子,我愿意多喝几杯水
- 下一篇文章: 312植树节只会养仙人掌番茄君教你零成